蒋绍愚:把“史”和“论”两方面结合起来
个人简介:蒋绍愚,1940年生人,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中文系副主任,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中心副主任、主任。1992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著有《古汉语词汇纲要》《近代汉语研究概要》《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唐诗语言研究》《论语研读》《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续集》等。

蒋绍愚在访谈中(吕宸 摄)
赵昕:蒋先生好,很荣幸今天能够和胡老师一起采访您。我们这次采访是为了庆祝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而组织的系列专访。我们知道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蒋先生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同学和老师们都非常期待能听蒋先生讲一讲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以及对一些有关问题的想法,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本次采访。
首先,关注凯发k8一触即发采访的读者,很多是我们中文系和北大的老师、同学,所以大家想听一听您当年在中文系的学习、工作经历,您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蒋绍愚:我是1957年入学,1962年毕业。我们毕业那一年北大中文系要在各科系开设写作课,所以我留下做中文写作课教员。一年以后,我还记得很清楚,王力先生当时是古代汉语教研室的主任,把我叫到他家里去,说:“听说你很喜欢看古书,你是不是愿意来我们古代汉语教研室?”有了王力先生这样的决定,我就转到古代汉语教研室,从第二年开始教“古代汉语”,是曹先擢老师的助教,最开始教中文系的63级,其中有一位就是现在的张联荣老师。此后一直讲授“古代汉语”。
1962年北大中文系1957级毕业生合影
蒋绍愚:文革以后我们古汉语教研室的年轻老师也逐渐多一点了,也开始招硕士生、博士生。我就逐渐不教本科生的“古代汉语”了,而给硕士生、博士生开课。主要是“古汉语词汇”和“近代汉语研究”两门课,还开过“唐诗语言研究”。我退休是2003年,退休以后返聘了三年,之后就正式退休了。我在北大的整个教学的过程大概就是这样。
赵昕:说起古代汉语,我们知道,现在中学教学里面,一种很重要的、大家非常常用的参考书《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也是您组织编写的,您能不能讲一讲这本字典的编撰过程?
蒋绍愚:这个说来话长。这本字典经过几次修订,到现在已经是第五版。我只说初版(1979)的编撰情况。
当时受政治运动影响,我们都要到工厂去劳动、上课。当时我就想,能不能做点事?当时工农兵“评法批儒”,需要看古书,我们可不可以这个为由头,编一本古汉语字典?用这个做理由,上面的工宣队也不能反对。
要编一本字典,第一个问题是确定搞多大规模、多少字。我提出一个初步意见,以王力先生《古代汉语》的“常用词”为基础选字,最后由王力先生逐字审定。文革过后,跟“十三经”索引、《史记》索引一对照,基本上全部符合。所以王先生的脑子里面装得很清楚,哪些是常用字,哪些不是常用字。
当时白天跟工人去参加劳动,晚上上点课,同时每周抽一定的时间,让学生一起做一些字条。当时商务印书馆倒是有眼光,愿意把这本字典拿去正式出版。那当然不能太草率,所以从1974年秋到1975年夏,一部分老师、学生和一部分工厂的工人就集中到商务印书馆编撰。当时从组织上讲是我负责的,但我的业务能力还不行,所以还是王力先生指导的。王力先生开头也住在商务,后来得到工宣队许可住在家里,我每周末把一周编写的字条打上包,回家的时候先到王力先生家里,把这一周的字条请他审阅。到第二周周末我再把一批新的字条给他,把他审阅过的字条拿回来。所以很大一部分稿子都经过了王先生的审阅,这样就保证了质量。1975年7月字典编写组解散,留下一堆散乱的稿子,我用一年多的时间把它整理加工后,交给了商务,1979年正式出版。这本字典1995年获首届中国辞书奖一等奖。

1974年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编写组合影(前排左起依次为:戴澧、王力、岑麒祥、林焘,后排左起依次为:蒋绍愚、张万起、唐作藩、徐敏霞)
赵昕:刚才听您讲了自己的教学经历,还有跟王力先生在一起工作的经历。您在以前的访谈中经常提到,您在教学方面很受王力、朱德熙两位先生的影响。您能不能具体讲一讲在哪些方面,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蒋绍愚:我自己回忆我这一辈子的生活、工作的情况,有两位老师我是感激不尽的,一位是王先生,一位是朱先生。王力先生的指导主要是编字典的过程,同时,他的著作给我指明了研究的方向;朱德熙先生对我的教诲和提携也很多,我内心也非常感激。但是他们在世的时候我不很多去打扰他们,在他们过世了以后,我倒是经常去看望两位师母。
所以我的印象里面,跟教学有关的还是我上学的时候。王先生给我们讲“古代汉语”,当时是在一教101这个大阶梯教室,里面挤满了听课的人,有人没有座位就坐在阶梯的地上。王先生讲课非常地清晰,不枝不蔓,重点突出。后来我自己在古代汉语教学里面,尽量向他学习,要尽量条理清晰,重点突出。
朱德熙先生给我们讲“现代汉语”。他的课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朱先生是一个非常严肃、正经的人,他上课的风格也是这样,绝不多讲一句学术以外的事情,那么他是靠什么吸引人呢?他带给大家的一种喜悦,一种探索的喜悦,以及探索以后有结果、有发现的喜悦。他往往先提出一些有问题的语法现象,让大家思考,然后就慢慢道来这个问题怎么看,给大家分析,他说到后来大家就恍然大悟。这是非常高超的教学方法,我自己在教学当中,也极力地想学习朱先生,但是我没学到家。
赵昕:您刚刚提到,您多年来一直在给本科生上“古代汉语”,后来又给研究生开和汉语史相关的课程,那么您对于现在讲授这些课程的青年教师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蒋绍愚:我一个总的想法,不论是讲基础课也好,讲专题课也好,不要“炒冷饭”。什么叫“炒冷饭”呢?就是一门课不会只讲一次,过了几年以后教案基本上有了,今年用的这部教案,明年还是这部,后年还是这部。虽然对于学生来说,听的对象不同,但是作为一个教员,我就觉得心里不安,我觉得这样就没有尽到老师的责任。讲义都发黄了,还照着这个讲义念,这是不好的。
那么基础课怎么出新呢?我觉得应该尽量使每一年讲课有新的内容,而这是可能的。因为学科不断地发展,研究成果也不断地更新,老师自己也要做研究,总归有一些新的想法。所以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内容,可以补充到教案里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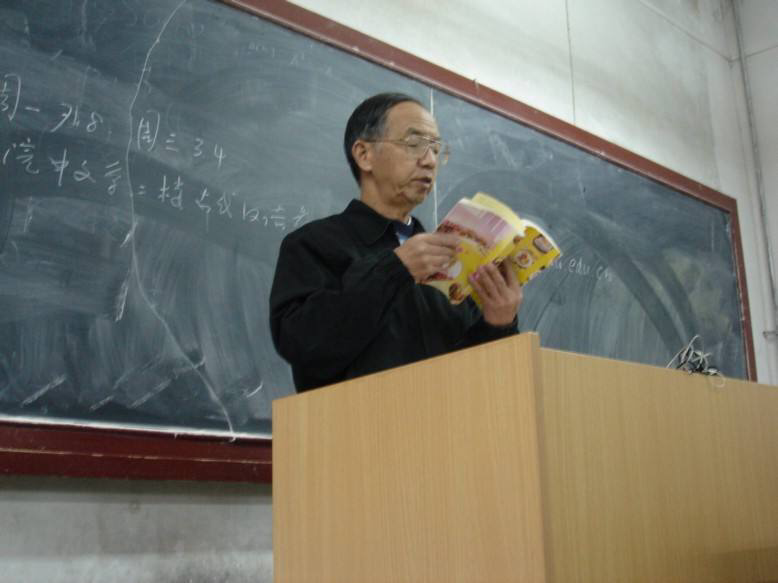
蒋绍愚在课堂(图片来源:北大档案馆)
蒋绍愚:就教师来说,每年讲课加进去新的内容,包括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和自己思考的新内容,把它积累起来,再系统化、加以扩展,就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成果。我的几本书就是这样写的,这一点也是向王力先生学习的,王力先生往往是开一门新课,就出一本新书。教学跟科研结合,这就是最好的途径。
如果说光是为自己的研究成果考虑,就把教学看作没有必要的付出,我觉得不能那么看。学术的发展是薪火相传的过程,每个人活在世界上的时间是有限的,你对学术的贡献,一方面是你自己写书、写文章、对学科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在精心培养的学生里面出一些很优秀的研究者,真正做到薪火相传,这就是对学术的贡献。你对学生的培养,也是对学术的一种贡献。
赵昕:您说对学生的培养,也是对学术的一种贡献,我们也知道您培养了很多优秀的硕士生、博士生,他们现在都成为了汉语史学界很重要的学者,您在培养研究生方面有没有什么心得能跟大家来分享?
蒋绍愚:这个问题我首先要说,所谓的“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各人”,学生的成绩,主要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他们取得的成就都是他们自己取得的,功劳不应该写在老师账上。
我对研究生培养确实有些想法。一个研究生在读的时候,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三到四年,为他今后的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一方面具备一些必要的基础知识,面要广一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思考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而不是全部精力只做一篇博士论文。如果全部力量都用在写博士论文上,而忽视了基础的培养,这就是舍本逐末了。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意味着博士论文不重要。它确实是博士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导师要有正确的指导方法:
第一,我历来主张论文的题目,要让学生自己选择。因为定题目本身也是一个学习和思考的过程。第二,论文的观点可以跟老师不同。这是我们北大的传统。重要的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说什么论点都可以,但是你要讲出道理来,而且有充分的事实来支持你自己的论据。不要以老师自己的是非来定学术的是非。另外,如果说论文中有的问题是导师不熟悉的,导师自己就要下一点功夫,来更新自己的知识。
2010年蒋绍愚参加在巴黎举办的第7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右起第三为蒋绍愚)
蒋绍愚:还有一点我也是有所感触的,我觉得在指导学生论文的时候是双向互动的,老师对学生有指导,给学生提出意见和建议,学生的论文也给老师很多启发。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有些外校的年轻人,愿意把文章或课题设计发给我看,我也还是愿意看,会给他提出一些意见。同时对我自己会很有帮助,他会把有关问题国内、外的论述写得很清楚,然后他自己也会在其中提出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现在年纪慢慢越来越大了,直接接触到这样一些新信息的机会比较少。如果能够通过这样一些论文或者是一些课题的设计,使我增长知识,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学习,对我很有意义。
我觉得在指导学生论文的时候,不要把老师当成工头,把学生当成打工的。如果老师让学生写论文只是为了给自己的研究提供材料,这就很不好。
赵昕:正像刚才先生讲的,如果我们的同学听课的时候能常听常新,又能够在这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环境中学习,一定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除了我们的同学,也有许多同仁期待您能分享一些治学的经验。您在汉语史学界是较早深入开展近代汉语研究的学者,您是怎样关注到这一领域的?
蒋绍愚:关于近代汉语,我确实做了些工作。但我屡次说过,我这个是“奉命而行”。我在《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的前言中说,在80年代初,朱德熙先生提出:北大中文系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方面力量都比较强,而近代汉语却没有人研究,应当补上。朱先生实际上还有下半句:“你可不可以把这一块做起来?”我当时听了以后,感到这个分量很重。近代汉语确实是汉语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这样的汉语研究是有断崖的,确实应该补。但我能不能挑起这个担子?
当时也是由于朱先生的指导和推动,我和北大中文系的几个老师跟社科院语言所合作编成《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为有兴趣做近代汉语语法的人提供了一些帮助。
另一方面我自己注意收集了有关近代汉语进展和研究的成果。所以我1994年的第一本书题目叫《近代汉语研究概况》,是研究状况的一些介绍。这里面虽然有我的取舍,但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观点。十年之后(2005年)题目就改作《近代汉语研究概要》,“概要”就不光是介绍别人的,我自己也有一些想法。到了2015年,又出了一个修订本,因为十年之间在近代汉语研究方面又有新的发展,一个是资料扩展,一个就是眼光扩展,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的更新。我把这些新的进展放到了修订本里面。
近代汉语的研究,我觉得首先要归功于两位前辈,吕叔湘先生的提倡跟朱德熙先生的推动。我自己只是受朱德熙先生之命,在这里面尽我自己的能力做了一些工作。

1984年社科院语言所“青年语言学家奖”首次评奖时留影(左起依次为李家浩、蒋绍愚、吕叔湘、郭在贻)
赵昕:您的研究兴趣中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面向,即“汉语历史词汇学”,它同传统的古汉语词汇研究在研究旨趣上有不少差别,您又是怎样关注到这个领域的?
蒋绍愚:我自己感到很惭愧,像你们这样的学术界新秀,念了书、念了博士以后就开始自己的研究生涯了。我的第一篇论文《杜诗词语札记》是1980年发表的,那时候我已经40岁了,比起你们来晚多了。那时我首先注意到,诗词里面有一些词的意思跟通常所说的意思不大一样。我把这些意思整理一下,写了《杜诗词语札记》和《唐诗词语札记》。
后来,我觉得如果我们对古汉语词汇光是采取一种训诂学的办法,一个一个词地去弄,还是不够,因为语言是个系统,所以应该对词汇做一个比较系统的考察,同时也要做一些理论方面的探讨。当时我参考了一些国外的语义学著作,得到一些启发,经过自己的思考,1989年出版了《古汉语词汇纲要》。在第一章的第三节里面有一个小节,题目就是“建立汉语历史词汇学”,但是什么叫做“汉语历史词汇学”?当时的认识也不是很清楚。后来,我在这方面继续思考,2015年出版的《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前言里面我说了这样的想法:对于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根据语料,描写汉语整个词汇系统的演变发展脉络和它的一些发展规律,这个是偏向于史的研究。另一方面需要对这些问题做理论思考。把“史”跟“论”两方面结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汉语历史词汇学。

《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书影
蒋绍愚:理论研究包括概念化跟词化、构式理论、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方面。我的《汉语历史词汇学》比起《古汉语词汇纲要》,所探讨的问题开阔了一些、进了一步,但是要说到汉语历史词汇学整体的理论研究和探讨,我这本书还是远远不够的。这本书只是一个尝试,后面的大量工作,是需要你们这样一些年轻的学者来做。
赵昕:刚才您分享了培养学生和自己治学的很多心得,我们大家听了以后都感觉到受益匪浅。现在想请您总结一下,一个优秀的汉语史学者应该具备哪些知识和素养?
蒋绍愚:首先,既然是汉语史,它就是一种史的学科,所以一定要熟悉基本事实。一定要比较扎实地掌握汉语史语料,并能够正确解读。
第二,做研究不是材料的罗列和堆砌。所以就必须有一个分析的头脑,需要分析的能力,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就是所谓的“两脚书橱”,即便他对材料很熟,但他一辈子也写不出有深度的文章来。
第三,要了解一些前沿的语言研究理论。做汉语史研究,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眼光,没有一定的理论思考,也是不容易深入的。但这里要防止几点:第一是不要贴标签,把时髦的名词贴上去是没必要的;也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仅仅是用汉语史的材料来印证某种理论观点,这个没有什么新东西。

2015年蒋绍愚在家中
赵昕:除了学者个人的因素,我们整个科学研究的发展,还有一个它自己的潮流和脉络。那么您认为,从宏观上看,在目前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汉语史学科中还有哪些需要我们集中力量来研究的方面?
蒋绍愚:我觉得是有这么几点,也是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第一点,目前汉语史的研究者基本上是给自己划定某个范围,比如,有人主要做上古汉语,有人主要做中古汉语等。这是必要的,因为汉语史确实历史太长,资料太多,一个人要从头到尾地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范围稍微小一点,这样也就更容易深入。但是从总体来看,汉语史各个阶段的连贯,注意得不够。要研究一个阶段从上看是怎么发展来的,往后看它是怎么演变的。
第二点,汉语史各阶段都有一些总体性的问题需要考虑。比如上古汉语跨度很大,为什么春秋以前和以后的语言面貌会这么不一样?上古汉语有不少王力先生所说的“词头”“词尾”,这反映了上古汉语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中古汉语,我和汪维辉、方一新等老师交换了意见,最大的困难,是不容易找到反映当时实际语言情况的语料。近代汉语的跨度也很大,晚唐五代的材料跟明清的材料比,面貌有相当大的差距。我认为这些大的问题现在都不能找到明确的答案,要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以后,再加以综合、概括。但是反过来说,做具体问题的时候,对这些大的问题脑子里要有一个自己的大致看法,如果完全没有大致的看法,只是做一个个具体问题,很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三点,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结合。出土文献的数量巨大,从先秦时代来看,是传世文献的好几倍,而且学术界研究得非常多,可以说是21世纪的一门显学;但主要集中在文字的考释上,而从汉语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做得不够。这么一大宗材料,如果我们研究汉语史不加以使用,这是非常可惜的。

2005年北大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获全国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赵昕:最后,您有什么建议想提供给我们中文系的年轻学生和青年学者?
蒋绍愚:我们的“古代汉语”系列课程在2005年获得了全国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这是第五届成果奖文科里面,北大唯一获得一等奖的,所以这是国家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荣誉。评语说:这门课程是“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五十年三代著名学者之努力”而建设成的。首先是王力先生、魏建功先生这些大师讲这个系列课程,后来才轮到我们这些小辈。总的来说,不论是古代汉语的教学,还是专题研究方面,北大中文系在全国都是处于领先地位。我总的一个希望是,你们这样一些后来人能够保持这样一种领先的地位。

2013年古代汉语教研室迎新年联欢会(第一排左起:孙玉文、宋绍年、郭锡良、唐作藩、蒋绍愚、张联荣、张猛;第二排左起:刘子瑜、宋亚云、胡敕瑞)
转载本网文章请注明出处